沈 淪
2009年,舉世矚目的三峽大壩橫空出世,全面竣工。臨近年關,飛雪迎風翩舞,如銀蝶追逐奔騰不息的大江激流,擁抱峽江兩岸翠綠的山巒……此時,一位老人信步氣勢磅礴的長江三峽大壩,透過眼鏡片上潔白的雪花,極目遠眺,雪浪飛虹,俯瞰高峽平湖的壯觀景致——這是繼長城之后第二個可以從太空用肉眼看得清楚的人造工程。本應該在葛洲壩之前誕生的三峽大壩,遲到了21年。此時此刻,發電、航運、種植、生態、環境等藍圖徘徊在這位老人寬闊的胸懷,演繹著三峽未來的獨特魅力。
這位老人,就是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水利工程專家、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文伏波先生。
從1949年跨出中央大學水利工程系校門至今,文伏波在三江四水寫下篇篇華章:
江漢平原第一項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荊江分洪;
南水北調的水源工程——丹江口水電站;
萬里長江第一壩——葛洲壩水電站;
享譽世界的超級大壩——三峽工程。
這4項工程,赫然構筑成治理長江開發史上4座不朽的里程碑,也托起一個水利學院士的傳奇人生……
曠世宏程寫天下
長江三峽大壩,猶如一架巨大的“古琴”飛架南北,滾滾激流,從遙遠的青藏高原奔騰而來,穿越大壩噴薄而出,如粗獷的琴弦,彈奏出震撼世界的東方旋律。這首“中國三峽水電交響樂”,第一樂章即1952年建成的湖北省荊州境內的荊江防洪工程,拉開了治理長江的序幕;第二樂章為l958年動工的丹江口水電站乃南水北調水源地的關鍵工程,具有防洪、發電、灌溉、航運及水產養殖等綜合效益,為南水北調彈奏出水往高處流的神話;第三樂章是把三峽水電交響樂推向高潮的葛洲壩水利樞紐。
正是以文伏波院士領銜的這個交響樂隊,演奏出了令國人驕傲、世人仰望的“長江之聲”。
“中國三峽水電交響樂”,史無前例,世界之最……這一幅幅國人的智慧與大自然巧妙融合的杰作,無不烙下文伏波先生的腳印。有詩曰:耄耋院士八十八/治水伏波當屬他/披星戴月走泥丸/笑飲風餐宿蘆花/荊江丹江闞長江/萬水千山繪三峽/胸懷田園寄家國/曠世宏程寫天下。
史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無獨有偶,文伏波在丹江口和葛洲壩兩工地,棲身20余載,乃至他年幼的女兒錯認文伏波的“眼鏡’’同事為自己的爸爸。
1951年,荊江分洪工程啟動,他除了參與工程設計,還擔負著工程質量檢查。白天親臨工地,晚上睡在竹棚里的拌攪機旁,和民工兄弟們滾在一起。
1954年,長江流域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流域性特大洪水。新中國成立后的長江水系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荊江分洪,在這次罕見的洪災中3次開閘分洪,經受住降服洪魔的考驗,保住了荊江大堤,確保了武漢市和長江中、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荊江分洪,還有漢江杜家臺分洪區,乃是文伏波在“水上長征’’的“處女行”。
1956年,長江流域第三步實質性的治理開始了,這是從平原進軍山地。他奉命參與了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設計施工,并擔任設計組組長兼現場設計代表組組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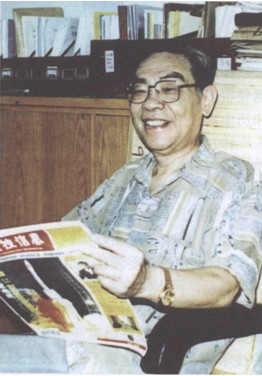
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文伏波記憶猶新。限于當時土法上馬、土法施工的歷史國情,又受到片面強調高速度的大躍進思潮影響,工地屢屢出現不按工程設計圖紙要求施工的情況,工程必然出現質量問題。他認真貫徹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的指示,嚴格按照設計要求,與施工方工程局展開激烈爭論。作為工程設計的負責人,面對這種不重視施工質量的行為,他的心懸在了嗓子眼上。身為科學技術工作者,他覺得,無論從科學的角度,還是從為人處事的良知,他都決不能沉默。否則,愧對于黨組織的重托。出于一個科技工作者必須堅持真理的良知,他冒著政治風險,不顧個人得失,利用各種會議和工地報紙,反復宣講和強調“質量是工程的生命,絕不能虛空求快,留下后患,坑害百姓,給國家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他因此與林一山一起得罪了不少人。
堅持真理,堅信科學。文伏波這種執著的精神最終獲得周恩來總理及時作出“停工整頓”的批示。
在停工兩年里,文伏波同工地廣大技術人員一道,代表設計方,針對當時施工中發生的各種質量問題,通過科學試驗和大量的技術分析,把原設計的混凝土大頭壩改為重力壩:采用楔形梁處理基礎施工中遇到的破碎帶;首次制定了國內系統的水利大壩工程質量事故補強措施……
實踐再一次驗證: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從竣工至今,歷經漢水流域1975年、l983年和l998年等特大洪峰的考驗,30多年安然無恙,為國民經濟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回首丹江口工程,親歷開工一停工一整頓一復工的全過程,文伏波奉獻了12個春夏秋冬。
在那個“特殊”的歲月,他不光是“靠邊站”,還成了“走資派"。不公待遇使很多同志想不通,但文伏波心胸豁達,意志堅強,以一種更高的政治覺悟和歷史責任感直面現實。
1970年陽春3月,文伏波“分配”做一份新工作——收拾院落垃圾。這天,忽然聽見喜鵲贊梅的悅耳之聲。頃刻,他接到時任長江委軍代表通知,迅速趕到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辦公室。
一進門,只見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體學在等他。文伏波和張體學可謂“冤家”,原來,早在丹江口工程開工時,張體學就是湖北省省長兼任總指揮長,文伏波是長江委派駐工地的設計代表。從此,針對丹江口工程的建設程序、施工質量,兩人時有爭論。盡管張體學是省級領導,文伏波只是工程設計方的工程師,但就工程而言,省里領導代表工程施工方,而設計方代表的是設計工程師,即施工必須嚴格服從科學技術。因此,施工方的總指揮也得服從設計方的技術員。這樣,他倆不得不較上勁了。終究,文伏波對事業嚴謹負責的態度和精湛的技術水平,在張體學這位德高望重的領導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因此,在歲月的磨合中,兩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誼。于是,在又一個天降大任的時刻,組織把葛洲壩再建奇功的繡球拋向了文伏波。文伏波和同志們立馬會師茅坪的長江水利委員會設計代表組。
葛洲壩當時預計修改設計的工期是3年。這么龐大的工程設計,3年怎么可能呢?回顧起當年夜以繼日戰斗在三峽工地的場景,文伏波發出爽朗的笑聲:“和丹江口一樣,l2個春秋,仿佛彈指一揮間。”
然而,葛洲壩開工伊始,走過一段彎路。l970年底,正值“文革”白熱化進程,葛洲壩工程僅憑一個規劃性的設計文件就倉促開工,怎么能滿足工程施工的需要呢?因此,在開工之初便陷入圍城之困。
 ◆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要點報告審查會聽取長江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文伏波(左)匯報,國務委員陳俊生(右)主持會議
◆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要點報告審查會聽取長江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文伏波(左)匯報,國務委員陳俊生(右)主持會議
1972年,周總理決定,主體工程暫停施工,重新修改設計。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室義不容辭擔當起重新設計的主體。在兩年的時間內,動員全部力量,會同有關兄弟單位,加強勘探試驗和科研設計工作,攻克世界性難題。為作好樞紐布置,不厭其煩地作了5個水工泥沙模型試驗,開展河勢規劃,協調大壩及其上游、下游的河勢;增加大口徑鉆探,摸清紅巖中的軟弱夾層分布數量,經過現場大型試驗,找出軟弱夾層的安全磨擦系數最小值;創造出“人”字門的啟閉設備,以及和意大利模型與結構試驗研究所合作開展了二江泄水閘的地質力學模型試驗,對二江泄水閘的變形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重新設計期間,文伏波先后擔任勘測設計團參謀長、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室設計代表處處長,在林一山的親自指導下,與同事們一起,大膽提出挖除葛洲壩小島;取消工程過魚建筑物,改為人工放流鱘魚;取消大江五孔泄水閘,代之以4臺l2.5萬千瓦的機組。這些敢為人先的建議在當時沒有可借鑒的經驗,加之特殊的時代背景,爭論異常激烈。
荊江分洪、杜家臺分洪、丹江口水利樞紐、葛洲壩水利樞紐和長江三峽大壩,這一系列長江水系的大手筆,建成至今,一直運轉正常,從未發生過重大事故。這些載入史冊的實踐驗證了以文伏波為代表的新中國水利人睿智的應變能力和征服自然的力量。
歷經磨難成大器
長江流域大江南北灑遍了他的汗水,一個又一個百年工程凝聚著他的心血,山川留下了他的足跡。在我們今天分享他的勞作所創造的幸福時,他的成就啟發我們,相信每一個不平凡的人,或者說一個偉大的人,必然是天才加勤奮經過磨練而再生。
難忘l949年春夏,新中國即將誕生。然而,長江流域中下游,1948年水災留下“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的凄景,恰遇一場近20年未見的大水災,造成無數堤垸潰決……
風華正茂的文伏波懷著滿腔報國熱情,在這年9月,等不及開國慶典的禮炮在北京天安門騰空而起,便打起背包告別校園,投身到災后重建和沿江勘察工作中,和黨政軍民一起堵口復堤。“我在堵口復堤、生產自救的勞作中,身臨蕭瑟的災后慘狀,作為一名新中國的水利學子,年輕的水利工作者,深感肩負重擔。回想起在江西彭澤縣城查勘時,‘數月不知肉味’,我們想改善一下伙食,竟然走遍全城沒嗅到一絲葷腥滋味,切身體會到水災導致的貧乏,內心深處更加堅定水利是安邦定國的事業。”從此,文伏波的一生與水結緣,寫就幾十年“披星戴月走泥丸,笑飲風餐宿蘆花”的艱苦歲月而又快樂的奮斗歷程。
1972年,周總理召集有關人員會商長江葛洲壩工程事宜,在翻閱匯報人員名單時,文伏波的名字引起了總理的興趣,總理風趣地說:“啊,文伏波,你這個名字到越南去不好——東漢時期征戰越南的馬援就被封為伏波將軍,搞水利卻不錯。你的名字不就是要降伏洪波嗎!”
總理的話,一語點破了文伏波人生宿命。用這樣一首詩解讀這位從桃江走出來的“當代大禹”的青少年簡歷——兵荒馬亂洪災泛/文家為國添英男/伏波立志降洪魔/金榜瞄準治水班/歷經磨難屢求索/獻身國民敢登攀/未等開國禮炮鳴/勘踏神州戰猶酣。
1925年8月,文伏波生在水鄉澤國——湖南桃江,常見水患。正因如是,為擺脫困擾祖輩幾代人的水患,父母對他寄予希望,遂取名“伏波”。文伏波青少年時期,處于大革命失敗后,中華民族動蕩不堪,老百姓飽受肌餓、貧困和戰亂之苦。然而,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文家父母見小伏波格外聰穎,于是咬緊牙關,節儉拉債,讓小伏波5歲就進了私塾。
艱苦的童年,催發他少年立志,積極進取,1943年,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學時選擇了水利系。
不久,日軍炮艦直逼南京,學校不得不遷到陪都重慶。l944年,國民黨政府面對日軍的攻擊不堪一擊,大片國土淪陷。上大二的文伏波毅然投筆從戎,參加遠征軍開赴緬甸。在殘酷惡劣的戰爭環境里,l0萬遠征軍死傷達6.1萬之多,年輕力壯的文伏波憑借自己堅強的意志和天生的體魄,鏖戰滇緬,堅持到抗戰勝利,繼而重返母校繼續學業,尋找報國之路。
人生夕陽如朝霞
雪花飛舞,春意盎然在即,仰望登臨三峽大壩之巔的文老,心曠神怡,夕陽的彩虹勝比朝曦,治江神曲響徹山川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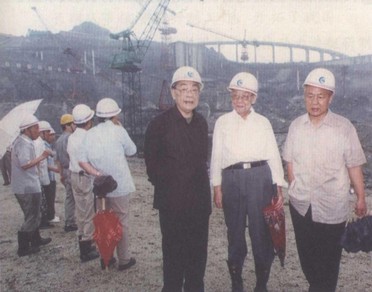 ◆在工地(右三)
◆在工地(右三)
文老一生雖然從事自然科學,其文史哲理修養也是一流,尤其在古詩詞方面造詣頗深,即使在艱苦作業的環境里也激揚文字,讓枯燥乏味的工地生活平添了幾分人文情操。
1959年,文老泛舟丹江口碧波萬頃于壩下,水輪發電機催人風發,于是欣然命筆《浪淘沙·丹江口有感》:
一九三五年/洪水滔天/漢江兩岸漫無邊/八萬生靈隨逝水/含恨九泉。
人民掌政權/干勁沖天/丹江口外筑石堤/防洪發電兼灌溉/福滿人間。
詩人情感細膩,發自肺腑,牽掛萬民。
1986年,文伏波把長江委副主任的接力棒傳遞給后來居上的水利人,擔任長江委技術委員會主任。
近年,他潛心于獎掖后學,扶持青年,鼓勵他們“多到前方去,到工地去,深入一線。”
文伏波先生一生為人十分謙遜,盡管他是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資深的水利泰斗,可是,他說自己永遠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熟悉文老的人們非常敬佩他,雖年逾古稀,仍時常堅持親臨長江三峽實地探索,對治江之情仍然濤聲依舊。常見耄耋之年的老者,多賦閑家中頤養天年。盡管近年來文老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每年去三峽考察,而文老一天都沒得閑。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己。”孟德名言,使人們從文老身體力行的歲月里,感受到文老這位新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有一顆金子般閃光的心。
正因為有一顆金子般閃光的心,以及淵博的學識和畢生積累的寶貴經驗,文伏波院士撰寫出《按可持續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要求進一步搞好長江治理開發》、《南水北調與我國可持續發展》兩部論著,向黨向祖國向人民又奉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禮!
